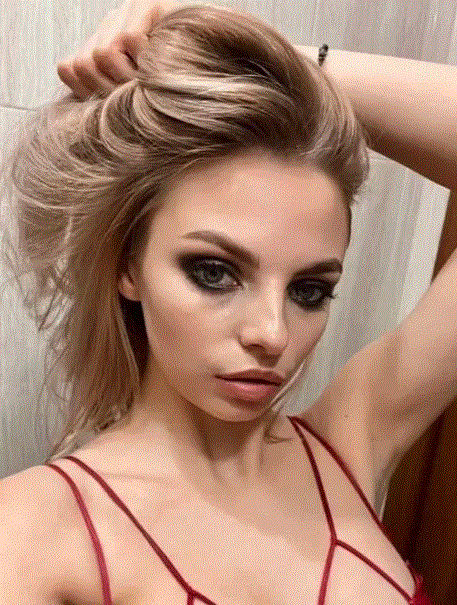语言的反向歧义是笑话和戏剧的常用手法
“妈妈,他拿咱家褂子啦。”“谁呀?”“逗你玩。”“妈妈,他拿咱家裤子。”“谁呀?”“逗你玩。”
——听到这几句词,脑子里该就有画面了吧,对,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就是这么深入人心。
“逗你玩”本来是一个行为,谁也没想到它会是一个小偷的名字。孩子越是告诉妈妈“逗你玩”偷东西,妈妈越是觉得这是孩子在故意逗着玩,反倒越没有警惕,小偷因为这样一个引发反向歧义的名字而轻松得手。
小偷起名叫“逗你玩”,不仅是故事里的人物连现实中的观众也一样没想到,出乎意料之外,又在乎情理之中,笑料就这样产生了。
“说了=没说”,语言因为反向歧义形成了一个死循环。类似的情节还出现在电影《甲方乙方》中,“打死我也不说”居然不是被拷打者坚定的信仰和口号,而是他想招供出来的接头暗号;于是,他越是急于招供,就越是招来更严厉的毒打。这段戏谑化喜剧情节不但令人捧腹,更让人记忆深刻,让人感受到语言反向歧义的魅力。
语言发生歧义的情况很多,反向歧义尤为特别,它所导致的结果往往是“越让你往东,你越往西”。所谓反向歧义,就是一个词语或语句所表达的意思恰好与它本身的含义相反。这样的效果,是戏剧、笑话等最求之不得的。
我的名字叫“无人”,奥德修斯的机智故事
语言的反向歧义甚至可以追溯到遥远年代的神话,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就有这样一个著名故事。
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率领部下驾船回国,途经一座海岛。一行十二个人进入岛上的一个山洞,他们发现了很多羊,还有羊奶、奶酪等各种奶制品。正当他们为找到食物感到高兴的时候,山洞主人回来了,这是一个硕大无朋的独眼巨人。
他进来后,用巨石封死了山洞。原来,这个岛上生活着一个名叫库克罗普斯人的独眼巨人部族。巨人发现了山洞中的海员们,奥德修斯想和巨人示好,但他不买账,一上来就拎起奥德修斯的两个同伴摔死吃掉了。第二天,巨人又吃掉了两个人。奥德修斯想用宝剑偷偷刺死巨人,但一想就算成功也无力搬开堵住山洞的巨石,只好作罢。随后,他和同伴们制定了一个新计划。
晚上,奥德修斯假意跟巨人套近乎,取出随身携带的美酒给他喝,问他叫什么名字,巨人说他叫波吕斐摩斯,然后回问奥德修斯叫什么,奥德修斯趁机说道:“我叫‘无人’。”巨人听完,醉醺醺地睡着了。
奥德修斯取出一根削得异常锋利的木桩插入火堆中,随即和四个同伴一起将点燃的木桩刺入巨人的独眼。巨人剧痛难忍,疯了一样乱扑乱撞,众人躲在山洞的一角,躲开了巨人的击打。巨人的怒吼声引来了岛上其他的巨人,他们询问波吕斐摩斯发生了什么?波吕斐摩斯痛苦地说道:“‘无人’骗我,‘无人’杀我!”众巨人听了很生气,说道:“你大概是病了,既然无人杀你,无人骗你,你还喊什么?你还是好好养病吧。”说完,都离开了。
盲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只好继续独自对付奥德修斯等人。奥德修斯和众伙伴一起,将山洞里的羊每三只绑在一起,然后一个人躲在中间那只羊肚子下面,将羊毛捆在自己身上。当巨人挪开巨石,到洞外放羊的时候,众人便逃了出来。
——原来,“无人”不是“没有人”的意思,而是某个人的名字。可一旦提到这个人的名字,听者就会误认为“没有人”。这和“逗你玩”的故事简直是异曲同工!
语言的歧义和语言的陌生性
“”逗你玩”居然是小偷的名字,“打死我也不说”居然是接头暗号,“无人”居然是某个人的名字……在这些有趣的故事当中,我们发现,当语言引发歧义特别是引发反向歧义的时候,我们所熟悉的语言突然之间变得“陌生”起来;而当所有真相被揭开之后,语言的陌生感又瞬间消失了,我们又回归到熟悉的语境当中。我们心灵在不知不觉间经历了“熟悉—陌生—再熟悉(恍然大悟)”这样一个奇妙旅程。
如果说语言歧义的“陌生感”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直觉性的描述,那么文艺理论家则把它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俄国学者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在其著作《作为手法的艺术》(或译《作为技巧的艺术》)中指出:
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 ,就是为使人感觉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 ,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 ,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
什克洛夫最早提出了“陌生化”这个概念,简言之,就是艺术常常以各种技巧和形式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从而加深人们对事物的体验和感知。
可以说戏剧、文学等利用语言歧义带给读者和观众的感受,正是这种“陌生化”的技巧之一。
这种陌生化,是让观者突然对一个自己无比熟悉的事物失去了“正常的感觉”,突然发现必须捋一捋思路才能反应过来,而在平时根本无需这么“迟钝”地做出反应。当观者顿悟后,陌生感才会消失,而此时作品已经达到了它想要“抓住”观者的目的。
还有一种极端的形式,则是让观者在“陌生化”的感受中持久地沉溺下去,因为始终找不到熟悉的感受,仿佛陷入了一座迷宫。将“陌生化”的语言变得熟悉,只能依赖自己的努力,这种过程就像猜谜或者开悟。
甚至可以说,利用语言文字歧义而形成的陌生化是一种捉弄观者的创作技巧。
《尤利西斯》:语言陌生化的典范之作
《尤利西斯》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 ·乔伊斯在 1922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描述了主人公利奥波德 ·布卢姆于 1904 年 6 月 16 日一天十八个小时在都柏林的种种经历。
小说运用了大量意识流手法构建了一个交错凌乱的时空。书中的文字有时语义和语法模糊混乱,有时大段落没有标点,有时冒出作者的自造的生词……故而被很多人称《尤利西斯》是一部当代“天书”。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这部书中大量运用了陌生化的手法,这已是此书研究者普遍认可的一个观点。
根据英国著名语言学家、语体学家利奇的观点,语言变异体指语音变异、词汇变异、语法变异、书写变异、语义变异、方言变异、语域变异、历史时代的变异等八种。这些变异在《尤利西斯》中均有所体现。
说得通俗一些,也就是说这部书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文字歧义。例如,乔伊斯杜撰了Outtohelloutofthat 一词,实际上这个词是由两个词组out to hell和out of that拼接而成,表达的是一种奇特的人生感叹,揭示了他们生不如死(out to hell),却又不愿死(out of that)的矛盾心理。
有意思的是,《尤利西斯》一书的书名别有深意。这指的是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尤利西斯”,而这位英雄在希腊神话的名字是“奥德修斯”,因为罗马神话和希腊神话有很多一致的人物和故事。奥德修斯,正是前文所讲到的“无人”故事的主人公。
从表面上看,这部书之所以以“尤利西斯”命名,是因为它的每一章都和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一个章节相对应,二者在人物经历、思想内涵等方面存在着隐含的平行、对应关系。
探谜君认为,关于本书的命名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似乎前人所未发,那就是“奥德修斯”的神话出现了语言歧义的情节(奥德修斯诈称“无人”),而这部著作也正是一部“集语言歧义于大成”的作品。故此,乔伊斯以“尤利西斯”命名此书正是对语言歧义(语言陌生化)的强调与暗示。
从语言歧义和陌生化的角度看《尤利西斯》译作的得失
1994年,《尤利西斯》的两本中译本几乎同时问世,一个是译林出版社的萧乾、文洁若夫妇合译本(上卷),另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金隄译本(上卷)。
自从两个译本问世后,由二者比较所引发的争论就持续不断,甚至译作者本人也参与其中。这里无意全方位比较两本译作的优劣得失,只从语言歧义和陌生化的角度来说一点感受。
前文已述,乔伊斯《尤利西斯》一书的重要特点在于利用语言的歧义、变异而营造出“陌生化”的效果,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两部译作中的一些细节,来看看谁更加贴近这一点。
原作中的一个词语萧文译本翻译为“小便”,而金译本翻译为“小水”。“小便”,所有读者都一目了然明白其意思,而“小水”则让大多数读者摸不着头脑。据金隄自己的解释,“小水”一词在《本草纲目》中指“小便”。有一些文学评论者就此一点而评价萧文译本通俗易懂,诟病金译本有故弄玄虚之嫌。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原著始终在强化语言的歧义与陌生化,那么,“小水”反倒是更接近于原著的主旨。就此一点,当以金本为佳。
通观整体,也会发现萧文译本有意降低读者的阅读难度,试图将原文一些怪诞的语句尽量翻译得“正常化”,而金译本则刻意与读者平常的阅读习惯保持距离,营造出一种陌生化的奇特氛围。
比如原著中的syphilisation是一个作者生造出来的词,萧文译本翻译为“梅毒文明”,金译本则翻译为“瘟明”。
在英文中,Syphilisation也是个不存在的单词,显然作者是将syphilis(梅毒) 和civilisation(文明)强行合成在一起,即便是英文读者读到此处也会一愣,对这一词语的陌生和歧义而展开联想。
不难看出,萧文译本的“梅毒文明”一词削弱了这种语言的陌生感,让读者能够很顺畅地阅读下去;而金译本有意用了一个在中文中也不存在的词:“瘟明”,从而比较成功地保留了原著所营造的陌生感。前者刻意追求的顺畅实则是代替了读者的思考,有意帮读者提前克服了阅读上的挫折,因此也就不自觉地过多掺入了翻译者的主观意愿。这个例子,还是以金译本为佳。
总之,语言因歧义而呈现陌生化,是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都爱使用的一种表达技巧,它使作品的艺术色彩更为强烈,一般表现为巧合、双关、谜语等特殊的气质。语言,在现实生活中的“客观性”,在艺术作品中被严重削弱,甚至彻底消失了。
参考书籍:
《古希腊神话与传说》;《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译本;《尤利西斯》金隄译本;《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什克洛夫斯基;《奇特的美——<尤利西斯>之陌生化》;《<尤利西斯>的“陌生化"解读》;《萧乾与金隄译<尤利西斯>恩怨》;《从语言变异处理手法看<尤利西斯>两译本》等。

 1989生活分享网
1989生活分享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