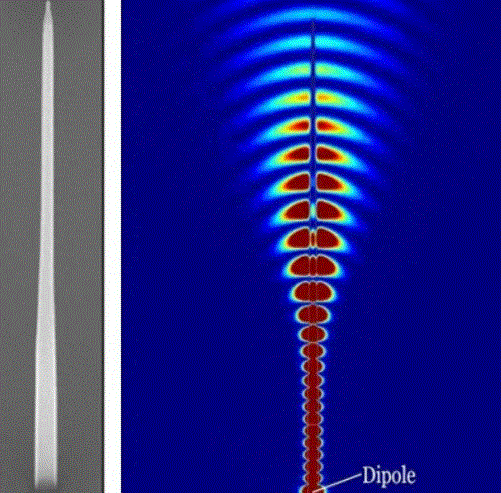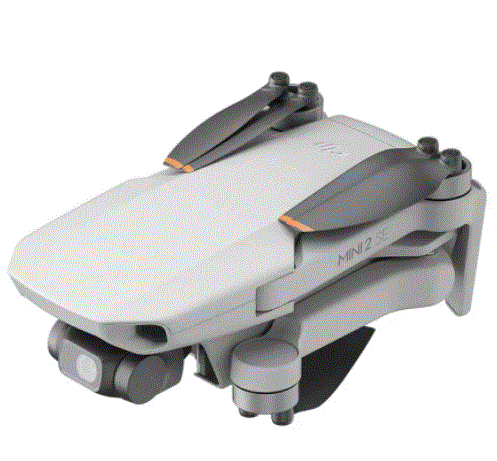文 | 《中国科学报》记者 赵广立
又有15位冉冉升起的科研新星。
10月31日,2022达摩院青橙奖名单公布。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研究员白蕊等15位青年学者获选。再过两天,他们将在阿里巴巴云栖大会上站上领奖台,从多位院士手中接过象征荣誉的奖杯。
阿里达摩院称这些青年学者为“科研摘星人”。何意?这些年轻人个个身怀绝技,“要做就做世界难题”——从探索浩瀚宇宙到拍摄“分子电影”,从求解数学难题到治疗“最毒乳腺癌”……他们踏上少有人走的路,执着地攀上科学高峰去“摘星”。
“摘星”之旅,曲高和寡。从2018年起,阿里达摩院每年遴选这样的年轻人,提供价值百万的“六便士”,助力他们抬头“看月亮”。这就是青橙奖——奖项的评选不唯资历、不唯履历、不唯论文、不唯门第,专为发掘35岁及以下杰出的中国青年学者设立。连续5年,青橙奖已颁发给50多位青年才俊。
今年的15位青橙学者,来自理论数学、量子物理、生命医学、化学材料、软件安全、端边云协同智能、第三代半导体等领域。这群平均年龄仅33岁的年轻人身上,有着他们特有的自信和锐气。
巾帼不让须眉!女性的价值更应被“看见”
2022达摩院青橙奖首次有4位女性科学家同时获奖,创出历年之最。
巾帼不让须眉,这4位女性科学家几乎一致地认为,没有哪个工作领域是存在性别障碍的,甚至觉得,社会越是进步,女性的价值更应该被“看见”、被尊重,女性应承担的责任越大。
白蕊在科研上取得的成就,让中科院院士施一公都赞叹有加:“如果没有敏捷的逻辑和辩证思维,我很难想象她是如何能从头设计出一条特异性高、效果好的 U12 型剪接体的底物,这项工作让我更加肯定她的科研天赋。”她和团队关于剪接体及 RNA 剪接分子机理的成果,已经被写进海外教科书。
这样一位“90后”女生,敢于挑战世界难题。她说:“真正困难的不是课题本身,而是有勇气去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士后出站后,白蕊选择继续做最重要、最难的基础研究,立志要“让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有更多的话语权”;她还要做有用的研究,“将研究成果用于相关疾病和药物研发上,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白蕊
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杨树的研究方向是氮化镓(GaN)功率器件(芯片)的设计、关键工艺和可靠性研究。她研制出高压、高频、高效的新型垂直氮化镓功率器件,攻克了长期困扰该器件的动态性能退化难题。
在杨树成长和求学的过程中,家人从来没有觉得女孩子就应该如何,或者是不适合去做什么;导师也是如此:“读时,我的工作量比周围的男同学还要大一些,也有机会去参与很重要的研究课题。”
不过,杨树也注意到,从求学到科研,再到高层次的首席科学家,女性的比例确实在不断下降,“几乎在工作后的每一个阶段可能女性都会遇到上升的阻力或是放弃了”。
也正因此,杨树很愿意为关注女性科研工作者的公益事业尽一份力。她现在是中国电源学会女科学家工作委员会的一员,“会关注女性科研工作者的成长和发展,尤其是面临的困境,”她觉得,女性做科研也有其独特优势,比如更敏感、更细致,会提供不一样的视角,会注重沟通和团队协作、更有韧性等,“如果大家都勇于追求梦想,或者被给予相对公平的机会,我觉得女性也可以有一片广阔的天地。”
杨树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特别研究员同丹关注气候与能源,她在读期间做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事:在全球尺度上收集了大概10万家各类厂房的设备级别的基础排放数据。这种尺度上的数据收集与开发对科研和决策意义重大,同时也颇具难度。以这项研究为基础发出第一篇Nature后,她逐渐在科研上开了窍,作出许多原创的重要工作。
看到欧美国家在气候变化研究中比我国领先一步、几乎垄断话语权,同丹希望能够用自主的数据和模型,“为提升我国的气候变化治理领导力做一些真真切切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事情、也很难,但老师总跟我们说,如果我们都不敢去想,中国还有谁会去做呢?”同丹说。
女性的标签不会成为同丹的牵绊,也不会阻止她和更多女性的在这个领域发光发热。同丹说,她身边很多女性科研工作者,她们在病床上、临产前还在改论文,“新时代的女性还是很不一样的。”
她也成为首位在孕期参评获奖的青橙奖得主。“我以前觉得怀孕的阶段或生小孩之后,会对我的工作产生一些影响,但我现在觉得,这些影响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我已经生孩的同事给我化解了许多焦虑和压力,她们真的可以把家庭跟工作平衡得非常好。”
同丹
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及数学科学系教授吴昊是青橙奖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女数学家。她曾经用7年时间,与合作者证明FK-Ising模型的连通概率猜想。做完后,跟这个课题相关的论文有65页——这还不算前期的很多文章。
她是教师,是数学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她一周有两天要教课。这两天除了教课,她会尽量把一些“其他事情”也安排在这两天,争取剩下三天是完整的,“这样可以做科研”。
她从不觉得女生不适合学数学。“更多是社会因素影响。”她分析,因为这个圈里女生少,所以女生更不敢进来,就造成女生越来越少。
吴昊的两个孩子都是回国加入清华后这几年出生的。孩子还小,她这几年在家庭上花的精力相对较多,科研“就先放慢一点”。相对自由的生活节奏,她觉得很满意:“我要保证每天工作八小时,但我们没有任何工作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只要你想做研究都可以做。”
吴昊
投身基础研究,他们敢闯“无人区”
今年获奖的15位青年中,有六成来自基础学科。他们中有的在领域最前沿初窥门径、沉醉其中;有的已经闯入“无人区”,不断向世界级科研难题发起挑战。
清华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杨杰从事了一个非常冷门的研究——拍“分子电影”。
所谓分子电影,就是通过研制科学仪器,实现对分子结构演化的直接捕捉。过去百年来,科学家发展的各类微观观测技术都只能捕捉物质的静态结构,无法捕捉动态运动。而要深入理解各类分子发挥功能背后的微观机理,就需要拍摄“分子电影”。
当时,“分子电影”这个领域仍然处于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严格来说是没人做成过。“有一些前辈做出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没有真正看清楚原子是怎么运动的,因此领域也在逐渐萎缩。”到杨杰读时,气相分子电影只剩下他们一个课题组了。
没有抱怨和质疑,杨杰闯出来一条路。他通过通过发展兆电子伏超快电子衍射(MeV-UED)技术,突破了原子级时空分辨率的仪器需求,实现了分子结构演化的直接捕捉。
2015年起,杨杰在美国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领衔发展了MeV-UED技术在气相、液相化学中的科学应用。作为首个实现这一突破的课题组,他们很快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科学成果。
“我们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是新的,基本没有什么竞争者。”杨杰说,因为冷门,这个领域的研究,如果他们做不出来的话,恐怕就没有人能做出来了,“那样的话对科学发展也是很大的遗憾”。
杨杰
同是做观测,但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助理教授吴嘉敏要突破的,是传统显微成像局限。
此前,生命科学研究大多局限于体外观测,在活体内观测挑战非常大,尤其是尺度范围非常广,很难在很大的视野拥有很高的分辨率,“好比是在体育馆里面去追踪几百万、几千万乒乓球的高速运动”。
但吴嘉敏就是对这种观测更感兴趣——大量不同种类的细胞到底是怎么形成器官,并产生对应功能的?大脑有意识、有认知决策,但每个神经元都不独自具备这样的能力,为什么能产生这种群体行为的功能?他希望通过技术的革新,去打开探索这些奥秘的大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吴嘉敏参与开发了一系列介观活体的显微成像仪器,让人类第一次可以在哺乳动物体内去研究大规模细胞之间的交互作用。
他是怎样做到的?答案是,把自己变成“交叉学科达人”。他自述:“我原来是做信息科学的,到光学领域是一个新人,要补一些光学知识,光学的人认可我也需要一段时间;光学上做得比较好了,我又要能跳到生命科学里,又是妥妥的一个新人。”
就这样,吴嘉敏通过计算成像方法,突破了传统显微成像局限,显著提升了活体成像的时空分辨率与数据通量,并极大地降低了光毒性。他参与的代表作之一是,首次实现了小鼠活体连续6小时以上的毫秒级亚细胞分辨率三维动态观测,相当于给观察细胞水平的活体小鼠架设了一台“上帝视角”显微镜。
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鸿曾现场参观吴嘉敏参与研制的多维多尺度计算摄像仪器——这是迄今国际上视场最大、通量最高的介观显微镜。他评价说:“这是我国先进显微仪器的杰出代表。”
著名数学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曾作过“青蛙和飞鸟”的比方——前者扎扎实实,在一个领域扎得深;后者飞得很高看很远,善于开拓新域。
有了新工具,就有希望结合一些新方法探索新发现。“我原来更像‘青蛙’,现在我努力做得更像‘飞鸟’,希望提出一些原创性问题,建立一些新的范式。”吴嘉敏说,这是他下一阶段的目标。
吴嘉敏
与许多科学家不同,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邵立晶经常开玩笑,自己是一个 “Useless Doctor”(无用士)。
其实,在引力天体物理领域,邵立晶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中科院院士武向平、蔡荣根给他的评价非常高:“是我认识的青年科学家中的佼佼者”“ 邵立晶已经是国内引力波研究方向的青年领头人之一”。
提出多种检验引力的新方法,改进引力波模版协助发现数十例新的引力波,深度参与过几个人类基础学历史上的重大发现——2017年人类首例双中子星并合的探测、2019年人类首张黑洞照片的拍摄、今年5月人类首张银河系中心黑洞照片的拍摄……邵立晶却说自己的研究可能是“无用的”。
“我们探索的是一种非常本质的东西,但我自己涉及的这一块,至少在这个时代是不太有用的,不知道什么时代能够用上。”他坦承,从知识到技术,路很漫长。
这是最基础的探索研究,也是邵立晶眼中“最治愈”的研究。
“研究天体物理后,你就知道自己太渺小了,不要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这个世界缺少你不会怎样;而这样渺小的生物又非常伟大,人类能够了解非常深刻的、宇宙的一些真理。”邵立晶笑说,他亲眼见过学习天体物理治疗焦虑的实际案例。
尽管做着“无用的”研究,邵立晶还是希望尽量扩张人类认知的边界:“如此,人类的知识体系就变得更大了。”
邵立晶
“青橙”的品味:基础的、重要的、急迫的……
2022达摩院青橙奖,还有一位跨界到临床医学系统的获奖者,这个人就是江一舟。
34岁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研究员江一舟,每天要面对被称为“最毒乳腺癌”的三阴性乳腺癌。这是临床上治疗效果最不理想的一类乳腺癌,患病人数又多,跟所有白血病患者的人数相当,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健康问题。
江一舟每年主刀乳腺癌手术400例,门诊患者一年近3000名。但立志成为一名“临床科学家”,跟他曾主治的一位病患有莫大关系。
那个不幸的病患是一位年轻的母亲。那时还没建立起指导三阴性乳腺癌个体化治疗的四分型系统——“复旦分型”(后来被多个权威临床治疗指南收录),没有精准治疗,更多还只能靠化疗去医治。后来,她的病情出现了复发转移。她跟江一舟说,自己并不惧怕死亡,但为了年幼的女儿,她愿意倾尽一切。后来,她变卖了房产,远赴美国寻找更好的治疗机会。但仍无力回天。
这让江一舟触动很大。“一方面,你要做一个临床上技艺精湛、对患者很温暖的医生;但光有这些其实不够,手里的‘武器’有限,还是没法控制病情。怎么办?”
他立志做一个临床科学家,针对三阴性乳腺癌去攻关,去找寻背后的答案。
但兼顾二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心血和努力。为了一边做临床一边做科研,江一舟把每周的时间分成了两部分:周一、周二,以及周三、周四白天专注于临床工作,剩下的时间会用于科研。
在这条路上,他的导师邵志敏教授是个学习的榜样。临床上,邵志敏的门诊几乎不限号,“不想让任何一个慕名而来的人失望”;科研上,他时刻瞄准临床上没有解决的难题,去展开系统的研究。
“我也希望能像导师和一些前辈一样,成为优秀的临床科学家,能够做值得托付的好医生,做真正有用的好研究。”江一舟说,这是他的终极目标。
江一舟
“领域一年比一年丰富,‘大神’一年比一年多”,达摩院青橙奖在学术圈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其社会效益也逐步显现。尤其是从今年15位获奖者以基础学科研究居多的情况来看——投身基础研究往往意味着长期不被人注意和“甘坐冷板凳”,青橙奖做到了激励青年科技工作者“十年磨一剑”的初心。
“青春本涩,热望成橙”。青橙奖要寻觅的,是“青春、激情、坚韧、责任、担当、理想的代言人”,达摩院相信的,是“技术有温度、科学有力量、研究推动社会进步、科研助力国家发展”。连续5年邀请青年科学家专心“看月亮”,且触角越来越“偏向”基础学科领域,达摩院设立青橙奖的意义正得到进一步彰显。

 1989生活分享网
1989生活分享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