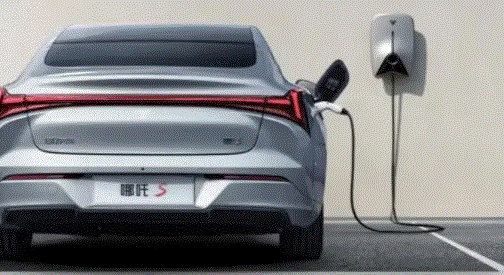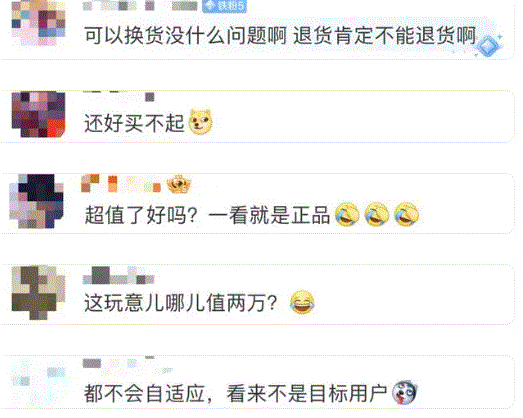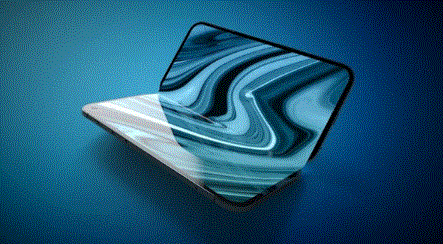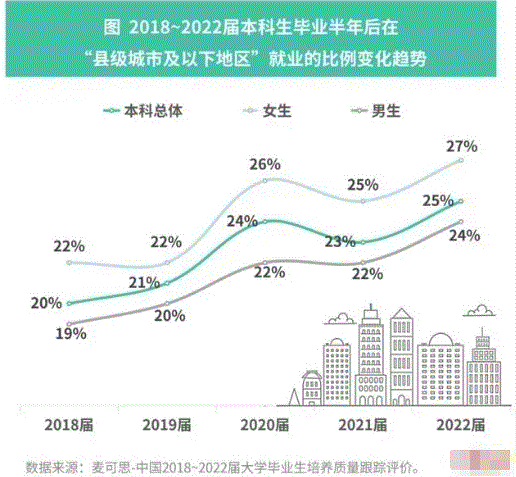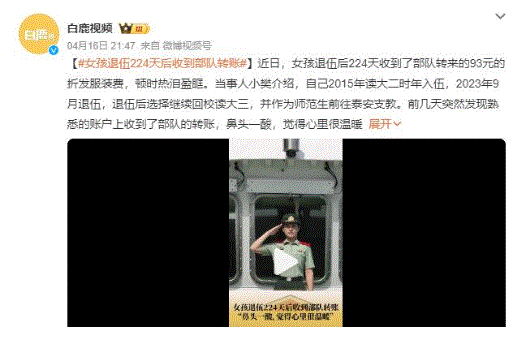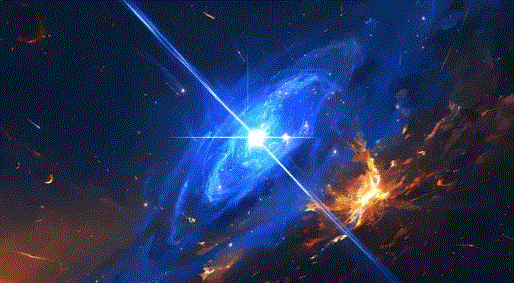澎湃新闻记者 喻晓璇
【编者按】
20年前的9月11日,美国纽约的世贸大厦遭两架飞机撞击轰然倒塌,举世震惊。美国、无数受牵连的民众,乃至整个世界的运行轨迹都因之而改变。20年后,恐怖主义的幽灵仍不时在世界各地肆虐,全球反恐会否“越反越恐”?20年的时间,是否足以令人类看清“9·11”在历史长河中的影响?
澎湃新闻(www.thepaper)国际部自9月10日起推出“全球反恐20年”专题报道,从多个维度呈现“9·11”以来这20年如何改变了个人、国家以及世界。
2001年9月11日美国东部夏令时间上午8时46分40秒,一位并不专业的飞行员操纵着一件不可思议的“武器”——一架波音767客机,撞向了纽约世贸中心,飞机内满载的9万多升煤油在猛烈撞击下点燃了北塔。16分钟14秒后,另一件“武器”撞向南塔,100余万吨的玻璃、石头、钢材和近3000名遇难者的遗体,化成了一堆七层楼高的“坟山”。
随后的几天里,一位眼神锐利的阿拉伯男子出现在全球几十亿个电视屏幕上。对于许多人来说,他已然成为邪恶的化身。他乘坐了“9·11”事件中第一架撞击世贸中心的飞机,被认为是这起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这名青年名叫穆罕默德·阿塔(Muhamed Atta),是19名劫机者中唯一一名埃及人。在“9·11”事件之前很长一段时光里,他似乎一直沿着一条既定的埃及中产阶级道路前进,从进入名牌大学,到出国留学深造,一路奋斗,不断向上。然而在某一天,他突然偏离了那条路,转向了一个人们无法理解的方向。
穆罕默德·阿塔的证件照,“9·11”事件后反复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阿塔出生于1968年,那是冷战中的世界喧闹、激进、爆发的一年:法国刮起“五月风暴”,民权运动席卷美国,各国青年们迷恋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摇滚乐与嬉皮士风靡一时……而这一年的埃及社会,也正暗潮涌动。
“1968年是非常重要的年份,那是‘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的第二年,这场战争的结局至关重要,它直接导致了纳赛尔主义(编者注:埃及第二任总统纳赛尔的政治思想,结合了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和主义、反帝国主义等思想)的崩溃。”瑞士中东研究学者维克多·威利(Victor J. Willi)近日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采访时表示。
威利今年4月出版了《第四次磨难》(The Fourth Ordeal)一书,此书基于一百多位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普通成员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口述,讲述了自20世纪60年代末至2018年埃及穆兄会的沉浮——他叙事的起点,正是阿塔出生的1968年。
“纳赛尔对于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而言,是希望的灯塔。他是不结盟运动的一部分,也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背后的真正驱动力——这是让所有阿拉伯国家扭成一股绳的意识形态。”威利说道,“但是1967年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泛阿拉伯运动的脆弱和无力,这在埃及造成了一种幻灭。”
《第四次磨难》 维克多·J·威利(Victor J. Willi)著 2021年4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阿塔来自一个穆兄会重获新生的埃及社会,之后他又在欧洲与“基地组织”建立了连结。虽然这两种运动有着完全不同的议程、纲领和手段,但在理论上却又分享着同一种意识形态根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阿塔的生活轨迹讲述着20世纪政治伊斯兰运动(Political Islam or Islamism)的两条不同脉络,直到今天他的故事仍可带给我们有关暴力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反思。
一个恐怖分子的成年
阿塔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卡夫谢赫省,在拥挤、破旧的开罗吉萨郊区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他的父亲是一名严肃而专注的律师,在严父的督促下,少年阿塔的世界里几乎只有学习。1985年至1990年,阿塔前往阿拉伯世界最负盛名的学府——开罗大学学习建筑学。
“尽管我们或许并不了解阿塔,但我们可以看看他是如何成年的(coming of age)。”威利描绘着上世纪60年代末以及整个70年代少年阿塔可能经历的图景:1970年纳赛尔去世后,萨达特继任,学生运动迭起,埃及的“六八一代”们仍思考着如何告别纳赛尔时代,在一片混乱与迷茫中,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伊斯兰思想重新渗透进埃及的社会生活。
“从70年代一直到1981年,当时的情况是,萨达特总统利用了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一些政治伊斯兰团体来对抗埃及涌现的一些亲苏的共产主义运动。他开放了大量的清真寺,释放了穆兄会领导人,给他们参与民主选举的机会,穆兄会的时机来了。”与阿塔几乎出生在同一时代的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教授穆尔西·马哈茂德(Morsi Mahmoud)告诉澎湃新闻。
开罗大学 澎湃新闻记者 喻晓璇 摄
在阿塔的埃及朋友们看来,虽然后来的恐怖分子阿塔彼时算不上是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人,但他确实从那时起就显现出了虔诚的一面。在《洛杉矶邮报》的一篇报道中,多年以后,表弟伊萨姆回忆起少年时代与阿塔一同看电视的场景:“每当电视上的肚皮舞节目出现时,阿塔就离开了房间。”
上世纪80年代的开罗是各种思潮汇聚的海洋,也是各种行动策划者的天堂。拥挤的都市唯独缺少工作岗位,咖啡馆里挤满了无所事事的人,咖啡、水烟和万宝路香烟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萦绕在屋内,狭窄而凌乱的街巷中充满了轻柔的烟雾与闲言碎语——但并非所有对话都是闲聊。
“穆兄会领导人出狱了,他们看到同时发生的学生运动,开始主动与这些学生接触,说服他们加入穆兄会,而这些学生们确实这样做了。”威利指出,“这些学生所依靠的仅有两部文本:《古兰经》和赛义德·库特卜的《路标》(Ma'alim fi al-Tariq)(编者注:库特卜是埃及作家,教育家,逊尼派伊斯兰理论家,诗人。他是埃及穆兄会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领导者。),虽然这两本书其实都没有提供一种清晰的政治方案,但是他们看到穆兄会实际上有一种政治方案——一种在社会实现伊斯兰生活方式的方案。”
自上世纪80年代起,穆兄会在校园当中进行广泛招募。他们呼吁回归“伊斯兰基本原则”,并警告远离“腐败的现代化力量”,拒绝埃及向美国倾斜。与此同时,穆兄会开始参与民主政治,不仅跻身议会选举,还开始在大学等机构的工会(Syndicate)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席位。阿塔所在的开罗大学建筑学系也出现着同样的情况,也许是出于父亲“不要参与政治”的警告,阿塔似乎当时并未与穆兄会建立起联系,不过当几年后前往德国时,他确实加入了穆兄会在欧洲分支的工会机构。
1979年,总统萨达特带领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迈出了阿以和解的历史性一步。激进的埃及穆斯林们自然无法接受,曾经让埃及遭遇“大挫折”( النكسة,Naksah)的宿敌以色列居然就要成为埃及的友邻,萨达特此举也为自己两年后遭“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在埃军中的成员刺杀身亡一事埋下了伏笔。
英国《卫报》2001年的报道称,阿塔后来在德国的一位朋友描述着与他一起前往埃及旅行时的场景,据他的观察,阿塔有着非常传统的思想,他和很多埃及穆斯林知识分子一样,对萨达特总统遇刺前埃及与西方的交好有一种“最愤怒的偏见”。
就在萨达特遇刺的同一年,持续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爆发。“当时,一大批逊尼派穆斯林年轻人在伊拉克与什叶派的伊朗作战,他们是在伊斯兰运动的思想感召下进行着战斗,这也在影响埃及的青年们。”穆尔西教授也回忆到。
暴力还是和平?
从开罗大学毕业后,阿塔未能如愿获得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机会。1992年,在父亲的牵线下,24岁的阿塔前往德国继续研究建筑学。20年来的各方研究都认为,事实上,阿塔的极端化过程是在欧洲完成的,在这背后暗藏的也是政治伊斯兰运动从埃及发展出的两条脉络。
1996年起,阿塔开始频繁参加德国汉堡圣城清真寺(Al-Quds)的活动。当时,随着移民劳工数量不断增长,许多穆斯林在欧洲永久定居,源于埃及的穆兄会已经在欧洲各地发展出了谱系复杂的分支,他们集中在清真寺中活动,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堕落和两性关系的混乱常常是他们批判的主题,而复兴伊斯兰价值则是他们的奋斗目标。
穆罕默德·阿塔(左四)在德国参加学生活动
离开家乡的阿塔养成了一些新习惯,他蓄起了大胡子,每日做五次礼拜,常常去清真寺,在学术上也形成了不同于常人的“体系”。美国《Slate》在线杂志2009年获得了一份阿塔的硕士毕业论文,在这份论文中,阿塔展示了自己对建设叙利亚阿勒颇城市景观的野心:拆除高速公路和高楼,重建传统的巴扎和住宅,重建一个“伊斯兰东方城市”。
在1999年底取得硕士学位后,阿塔离开了德国。几个月后,远在几千公里外的阿富汗的一场斋月宴会上,一个名叫奥萨马·本·拉登的沙特人告诉他,“你将成为一名殉道者(Shahid)。”阿塔被告知自己将领导一项摧毁美国最著名、最现代的高层建筑群的计划。某种程度,这正与他硕士毕业论文中重建阿勒颇的设想不谋而合。阿塔或许已经感到那双命运的手在推波助澜,他欣然接受了这项使命。
美国调查人员认为,就在德国圣城清真寺,阿塔曾与极端分子会面,也有极大可能被本·拉登的“基地组织”特工直接招募。调查还认为,阿塔在圣城清真寺遇到的另外两名阿拉伯青年人——齐亚德·贾拉和马尔旺·谢赫也被吸纳成为“基地组织”成员,这两人后来成为了“9·11”事件中撞击双子塔的两架客机的飞行员。
如今人们的共识是,策划实施“9·11”袭击的阿塔,与穆兄会并无直接关联,而是受雇于“基地组织”。然而,这个至今被认为罪大恶极的恐怖组织,某种程度上,确实与穆兄会在理论分享着同一种意识形态根基,却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1928年,出生在苏伊士运河岸边的埃及教师哈桑·班纳创建了穆兄会。那时的苏伊士运河仍被英国殖民者把持,在当时的背景下,穆兄会的创立本是一种对西方殖民和现代化的回应,号召人们“回归传统,回归伊斯兰”。
虽然穆兄会的性质最初更多是社会和文化的,但这种理念与纳赛尔倡导的世俗民族主义格格不入,穆兄会与埃及政府的对抗也引起了组织内部思想上的巨大分歧,造成温和派和激进派割席。1981年刺杀萨达特的极端穆斯林,正来自从穆兄会分裂出的激进团体“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而“基地组织”现如今的领导人扎瓦希里同样来自于“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
“政治伊斯兰这个概念在上世纪20年代刚刚出现的时候,就一直有这样的辩论:使用暴力手段推动政治运动是否合法?事实上,在伊斯兰主义者内部,有一派人更关注‘达瓦’(Da’wah,دعوة,阿拉伯语原意为‘邀请’,伊斯兰教中指引人信道),他们更希望通过教育、布道的方式让他人皈依或是改宗伊斯兰教,但是另一派人说,不,我们无法只靠‘达瓦’,我们需要让它变成一项政治运动,要么就是参与政治议程,要么就是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激进,也就是在抵抗敌人的时候更加暴力。”威利指出,“这样的辩论一直都让政治伊斯兰运动愈来愈分裂。”
道路的分歧点集中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埃及穆兄会的重要人物——库特卜身上。库特卜认为,纳赛尔的统治和对穆兄会的高压政策让埃及回到了伊斯兰教出现之前的蒙昧时期(也称贾希利亚时期,Jahiliyyah),他鼓动人们通过“圣战”的形式对国家进行直接反抗。
库特卜1966年被判密谋颠覆国家罪,后被处以绞刑,他的弟弟穆罕默德·库特卜也被判入狱,出狱后,他来到了沙特继续传播库特卜主义。本·拉登的一位密友曾透露,本·拉登定期参加穆罕默德·库特卜在沙特的讲座,而他的继任者扎瓦希里也在自己所著的《先知旗下的骑士》中向库特卜致敬。
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进一步将政治伊斯兰运动带向了暴力的十字路口。抵抗侵略穆斯林领土的超级大国——这种“圣战”理念让中东的穆斯林们深受鼓舞,这场反苏独立战争吸引了来自中东和北非的无数激进分子。阿富汗成为了将政治伊斯兰与暴力连结起的纽带,也成了本·拉登全球“圣战”的“基地”。
“确实,埃及的政治伊斯兰运动与陆续打败了苏联与美国的阿富汗政治伊斯兰运动有很多联系,第一批奔赴阿富汗的‘圣战者’当中有很多都是埃及人,他们的很多思想最初也来自埃及播下的种子。”穆尔西说道,“但他们与穆兄会又有明显的不同。”
在“基地组织”不断招兵买马、为恐怖袭击训练如阿塔这样的“圣战者”的同时,埃及的穆兄会仍在为参与政党政治而斗争,尽管已经历数次镇压,但他们未放弃过在选举框架下获得执政合法性的目标。
穆巴拉克总统在位时期推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很多反对派得以重返政坛,穆兄会也抓住了机遇。2005年的议会选举中,穆兄会已经事实上成为了埃及现代历史上的第一大反对党(编者注:穆兄会成员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同一时期,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国家,与穆兄会身份接近的政治反对派也正进行着相同的努力。
“无论是穆兄会,还是突尼斯的复兴运动,他们在激进主义的边缘突然被‘基地组织’这种新的全球性的组织取代了。”研究政治伊斯兰运动的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费萨尔·德夫吉(Faisal Devji)向澎湃新闻指出,“基地组织”与此后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完全不同于穆兄会,“旧的政治伊斯兰组织的观念非常民族主义,尽管他们当然有自己对于穆斯林世界的愿景,但他们更倾向于在自己的国家之内完成这项事业。”
崛起、陨落、再临?
埃及穆兄会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末。“阿拉伯之春”从突尼斯席卷了整个北非,2011年1月25日开始,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数百万埃及人日日占据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18天后,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被迫下台,蛰伏已久的穆兄会抓住埃及政局突变的时机迅速走上了政治前台,来自穆兄会的穆罕默德·穆尔西2012年当选为埃及首位民选总统。
然而,穆兄会的上台没有让人民看到太多改变,更有人认为穆兄会“窃取”了人民斗争的果实,抗议在2013年之夏再度爆发。2013年6月30日,在穆尔西上台一周年之际,数百万民众汇集在开罗、亚历山大、塞德港等城市举行示威游行,其中既有穆尔西的支持者,也有其反对者。埃及政治局势再度陷入动荡,这位自1952年埃及独立以来首位民选、非军方背景出身的总统在就职一年后被亲手提拔的时任国防部长塞西推翻,黯然下台。
“阿拉伯之春”时期解放广场附近著名涂鸦“含泪吃面包男孩” 澎湃新闻记者 喻晓璇 摄
与前总统同名的穆尔西教授前往国外访问时常常会被问及有关穆兄会的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这不是他们的时代。确实,你需要在对的时间让一个对的人上台,我只能说,2012年对于穆兄会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时机,他们还不知道如何保持稳定,如何说服人民。”
“穆尔西犯的一个错误是,他让人们认为他已经掌握了国家的政治,然而他并没有。虽然他仅仅被放在了总统的那个位置上,但这却让人们相信一场真正的‘革命’已经发生了。”乔治城大学卡塔尔分校外交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阿卜杜拉·阿里安曾分析指出,“(当时埃及)这个国家,很大程度上仍由穆巴拉克手下的同一帮人掌握。”
2013年穆尔西下台后,埃及政府立刻宣布穆兄会为非法组织,500余名穆兄会成员被判处死刑,还有更多的穆兄会支持者受审。六年后,穆尔西在一场对于他参与“恐怖主义”与“间谍罪”指控的庭审中突然去世,终年67岁。几经浮沉的埃及穆兄会,再一次不可避免地陨落了。
“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几年内,与百余名穆兄会成员的接触让威利印象深刻。“我意识到,他们是历史的失败者。”威利说道,“这些穆兄会的普通成员们过着贫穷而艰苦的生活,他们是埃及社会的中下层……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他们受到了穆兄会领导人的误导,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基本上只是在谈论政治伊斯兰。”
除了扫除穆兄会势力之外,塞西上台后还面临着反恐和治安的难题。埃及东北部的西奈省地广人稀,地形崎岖,常年有极端分子活跃,在此般安全真空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趁势盘踞于此,以此为基地在埃及各地策划并实施了多起恐怖袭击。
2015年,塞西签署新的反恐法,并批准成立特别法庭,不过当时也有批评声音认为,塞西此举“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在新法颁布后不少穆兄会支持者和政治反对派也被逮捕。穆尔西教授认为,埃及政府对穆兄会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几乎采取了相同的“反恐”措施,确实有出于稳定政权的现实考量,但这种措施并不完全妥当。
“穆兄会经历了四次镇压,现在的情况,我们可以参考的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情况,当时整个埃及有大约100万穆兄会的成员。领导人进了监狱,意识形态还可以复活。”威利表示,“2013年以后,尽管穆兄会作为一个组织来说非常的脆弱、支离破碎,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意识形态死亡了。”
最近发生在阿富汗的戏剧性转折,也让世界目睹了一支强大的政治伊斯兰力量是如何重整旗鼓的。
“虽然政治伊斯兰可能会卷土重来,但它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因为它从未成功过,事实上直到最近它才成功。”威利说道,“伴随着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这种意识形态回归了,他们带着悍马车、阿帕奇直升机和战斗机、他们还有大批的步枪、夜视仪……看看今天的塔利班,他们就像是美国的战斗部队……是的,政治伊斯兰很大程度确实已经回归了。”
有分析认为,塔利班的成功对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伊斯兰运动或是一种激励。在加沙地带,与穆兄会密切联系的哈马斯已经致电塔利班领导人以示祝贺。埃及政府显然也警惕着事态的发展。
“埃及的穆兄会可否卷土重来?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问题,这取决于当前的埃及政府,以及这个政府可否真正为民众提供服务。”威利认为,假使现在埃及发生另一场“革命”(Thawrah),穆兄会依然会是一股强有力的候选力量,我不会完全否认他们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但是这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现在的埃及同样也很担心,倘若一些在阿富汗活动多时的‘圣战士’回到埃及,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伊斯兰运动,他们可能会采用与塔利班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埃及政府绝对不会允许这一点。”曾为埃及军方从事安全研究的穆尔西说道,“我认为政府一定会仔细审查那些从阿富汗来到埃及的人,无论他们是塔利班,还是‘圣战士’,还是阿富汗人……但是我认为,现在的埃及人并不需要这样的政治伊斯兰运动。”
“我们今天掌握的所有证据都表明,政治伊斯兰并没有一个可以被统一讲述的故事,因为在不同国家之间,它的表达、它的经验、它的未来轨迹迥然不同。”2017年,美国前国务院宗教与全球事务办公室高级顾问彼得·曼达维尔(Peter Mandaville)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一场讲座上说道。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段九州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胡甄卿
校对:刘威

 1989生活分享网
1989生活分享网